就「2014-15年度財政預算案」發言 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(“預算案”)多年來被批評得最多的是,政府每次都錯估收入,而且多屬低估,以致累積了很多財政儲備,不知如何使用。有時政府會以一次性的“派糖”措施,像炮仗般燒完後便甚麼也沒有。政府究竟應如何估算其收入呢?財政司司長在今次發表預算案前成立了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(“工作小組”),就此作出了一些估算,根據過去30年的歷史數據估算將來的收入。 以歷史數據作出估算其實是很合理的方法,因為這做法可涵蓋剛才提及的很多因素,例如各種稅制的改變、社會服務的增長、各種爭議等。以歷史數據作出估算本來是很合理的,但細看其細節,據預算案第131段所述,過去30年的歷史數據顯示,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幅是每年平均4.6%。既然過去30年的增幅是4.6%,對未來30年的增幅也應作出相若的估算,但工作小組對未來二、三十年的實質增長估計原來只得2.8%,不知為何調低了,而這似乎滲入了一些人為因素。以歷史數據就將來的情況作出估算是很合理的做法,但政府卻在得出估算結果後調低了增長數字,調整幅度究竟有多大?似乎真的要神仙才能知道政府是否正確。
如此專業的問題,我不打算爭論,只會嘗試以另一方法考慮事情:如果政府的估算正確,將會如何?若估算錯誤,又將如何?由於只會出現對或錯這兩種情況,我們便要討論將來應如何打算。我姑且當政府的估算正確,那麼財政司司長提出了甚麼建議?他建議採取控制開支、收入保障、未雨綢繆等老生常談的做法,就此我特別從醫療方面的情況作出討論。
如果政府的估算正確,財政司司長就如何控制開支在其預算案第139段提出,“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需檢討開支情況,研究如何提升效率,厲行節約,力求事半功倍,以較少資源達到較大效益。面對社會各方面的需要,我們會繼續增加經常開支”,諸如此類。不過,問題正在於此。第一,無論財政狀況如何,第139段所述的事情也應實行,不單沒錢時要這樣做,有錢時也不應胡亂花費。第二,我們應如何實行第139段所說的事情,特別是在醫療方面?
政府要求醫院管理局(“醫管局”)提升效率,力求事半功倍,但現時的撥款方法並非如此。現時的做法是每年給醫管局一個“大信封”,在計算每年的人口增長、價格調整、通脹等之後每年增加3%撥款,然後任由醫管局自行安排提供各種服務。假設7年後,政府的估算正確,不能再增加撥款,醫管局便會以撥款減少為理由延長輪候時間,令病人需要等候更長時間,服務將會倒退。其實,今天大家已經眾口一詞,要求增加對醫管局的撥款,屆時財政司司長如何應對?而且我想特別強調,通常在收縮開支或沒法增加開支時,最大阻力往往來自員工方面,所以,當局能如何未雨綢繆呢?
我認為司長若繼續以“大信封”形式分配撥款,特別是醫管局這類機構,那將行不通,因為政府屆時根本無法承受公眾的壓力,而且當醫管局的服務越趨差勁時,政府如何可作出控制?所以政府承受的社會壓力將會很大。因此,我建議司長除撥款予各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之外,有時對一些宏觀的重要政策,特別是醫療政策,也需要有直接的參與。
舉例來說,如果司長認為其估算正確,7年後可能會開始出現結構性赤字,屆時的醫科畢業生將多數不能找到工作,因為“三軍未動,糧草先行”,政府如削減撥款,醫科畢業生便會找不到工作,那麼第一,政府應由2015年開始削減醫科生的數目。
第二,正如我以往多次提及,醫管局服務欠佳是因為其內部資源分配不均,並非每個聯網的輪候時間都這麼長。兩個星期前,“新聞透視”終於聽取了我的論述,拍攝了一個特輯,揭示有些聯網由於財政撥款無論如何增加,長久以來所獲分配的資源比例均持續偏低,所以那些聯網的輪候時間永遠都那麼長。報章亦有報道,指港島西的康復病床佔用率不足六成,而其他聯網如新界西的佔用率卻超過九成。因此,如果財政司司長向醫管局增加的撥款並非投放在市民最感不滿之處,則無論增加多少撥款也不能改善其服務。所以,我的要求是政府應直接參與制訂宏觀的醫療政策,微觀的且暫時按下不表,但這做法其實可在無須增加資源的情況下改善服務。
此外,政府亦需要設立獨立的審計機制,看看醫管局提供的服務有否如司長在預算案第139段所提出般有不合時宜或重疊的項目。現在如不這樣做,以我們的醫生同業如此精明,政府將無法令他們削減服務。
如果工作小組再次錯估,香港未來30年的經濟增長原來跟過去30年一樣強勁,那又該怎麼辦?香港又累積了巨額財政盈餘,政府原來有能力持續增加撥款,但如果聽信了我的建議削減醫科生,屆時便有很多撥款和空缺,又會招來責罵,那該怎麼辦?有見及此,我們是否可以引入一種較新的概念?
很多時,司長被批評是守財奴,有錢不花的原因,是由於在香港的實際環境和稅制中,有很多財政收入是屬於一次性的,亦即當經濟繁榮時,賣地會特別多,又或諸如此類的原因,會有一些一次性的收入,但司長表示要控制的卻是經常性開支。對於這些經常性開支,一旦失去上述的一次性收入,便會變得沒有資金可花。在這方面其實能否彈性引入新概念,除經常性開支外設定一些半經常性的開支呢?換言之,部分開支可在取得社會共識之下,在有錢時才支付,沒錢時則省下不用。 在醫療方面能否有這種彈性的安排和調整呢?若政府把錢全部撥交醫管局,以其情況而言應沒有這種彈性。只要政府撥款給醫管局,有很多事情便不能控制,例如就目標而言,醫管局會全數聘請常額員工,政府將難以削減其開支。較彈性的做法是,政府其實可就某些範疇,以醫管局的成本價直接購買服務。在今年的預算案中,政府一定是聽取了醫管局或高永文局長的建議,所以提出撥款4億2,000萬元推行大腸癌篩檢先導計劃(“先導計劃”),我可以此為例作出說明。
大腸癌篩檢如何運作?以外國標準做法而言,所有50歲以上人士若有此意願均可將大便送交醫院作隱血測試,驗出有大便隱血的人士可進一步進行大腸鏡檢查。一般而言,大概有2%人士會被驗出有大便隱血,而大腸鏡檢查的費用則最高。大便隱血測試的成本約為每人數百元,但在醫管局進行大腸鏡檢查的成本則為1萬元至23,000多元,不僅昂貴,還要輪候6個月。政府既然願意撥款4億多元推行先導計劃,醫管局提供檢查服務的成本又如此高昂,而且須等候多時,一個很簡單的做法是交給私人市場進行。
私人市場的情況如何?首先無須等候或最多等候1個星期,這總比等候6個月為佳,而且私人市場中這種標準大腸鏡檢查的成本,我猜大約是1萬元,較醫管局還要便宜。我不知這事將來會有何發展,因為衞生署一個小組仍在研究其細節,但若能選擇,大家會選擇在醫管局還是私人市場接受檢查呢?選用私人市場服務除了無需等候之外,病人若怕痛亦可選擇多付1,000元至2,000元,要求進行麻醉,又或反正要做照鏡檢查,不如順道同時檢查胃部,所以當中有很大彈性。
最可貴的是,正如我剛才所說,這可以是半經常性的開支,何解?例如在7年後,政府因欠缺財政資源而中止這項服務,相信也不會有很大反彈,因為進行大腸癌篩檢的人士全部均與一般正常人無異。以外國經驗而言,即使政府斥資讓人們接受檢查,很多人也不會使用這服務,一般只有六成人士接受檢查。所以,司長大可在各個領域中,以及和張局長探討在福利範疇及各種社會福利方面,可否引入半經常性開支的概念,在已有協議的情況下,在有錢時推行某些服務計劃,並以例如5年為限,但沒有錢時便不再提供有關服務。如此一來,政府將來便會有較大彈性,可因應政府收入的短期增加或減少,作出具彈性的安排。
我剛才假設當局的估算正確而提出削減醫科生,有些人可能會以為我瘋了,因為現時的醫療服務欠缺大量人手,我竟然還要求削減醫科生。我想在剩餘的少許時間內再次提出一些簡單的想法,因為大家總認為公營醫療服務差勁的原因是人手不足,但我剛才已解釋公營醫療服務差勁,很多時可能是由資源分配不均導致。提出醫療人手不足的朋友包括政務司司長曾經指出,醫管局現時欠缺300個人手,情況很差。然而,有較多行政經驗的人士一算之下,便會發現所欠缺的300個人手相對於醫管局5 500名醫生而言,所佔比重約為5%。那即是說,在一個有20人的部門編制下,只缺1人會否對所提供服務造成重大影響呢?若說會也只是騙人而已。相反,多提供300個人手,是否代表醫管局可即時改善至能夠提供市民滿意的服務呢?一定不能。
很多人怪責香港醫學會,認為該會反對輸入海外醫生,以致醫管局的服務受到影響。我希望向他們進一言:雖然香港醫學會反對輸入海外醫生,但其實是反對無效,因為醫管局有刊登廣告並篩選申請人,然後就認為符合要求的申請人提出輸入來港的申請,且差不多全數獲批,只有1人不獲批准。所以,聘請海外醫生這方法其實效用有限。部分人士希望放寬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規定,爭議之處在於是否需要他們考試。但是,如無須他們應試,將有更多醫生私人執業,若要應試則正如我剛才所說,名額已滿。最後一句:車神冼拿若復活並來港駕駛,他又可需要考取本地的駕駛執照?
代理主席,我謹此陳辭。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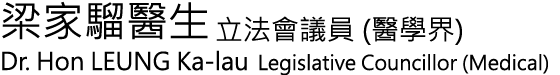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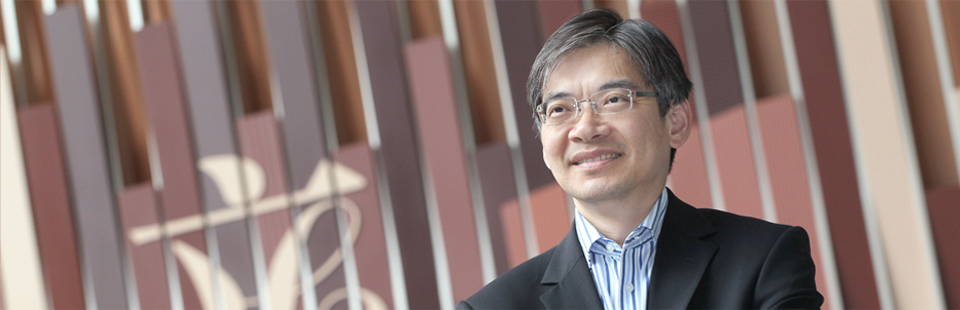

 / 4 頁
/ 4 頁

